黄孝纪的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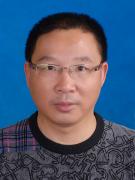
黄孝纪
文章:41|日志:1|访问:148007-19叫花子来了
“叫花子来了!”
村前的石板路上远远地出现一个陌生的人影,突兀在碧绿的稻田之间,拄着一根长棍子,胸前斜挂
07-18再见老井
老井枯干的那些日子,村庄也病病殃殃地打不起精神来。确切地说,因了高速铁路线的修建,沉静数百年的村庄在忍受一场
07-17扯花生,捯花生
近些日子,我所寓居的小区菜场,陆续有时鲜的花生在卖。余姚的卖花生,与我家乡甚是不同:乡下上了年岁的男女村民,
06-07晓明和他的诗
黄孝纪
几天前,晓明从广东打来电话,说他准备出版一本诗集,是香港书号,拟回老家印刷。我脱口说,香港书号在
05-24地仙
黄氏宗祠高大的中厅门口两侧贴着白纸对联,宽阔的中厅里铺陈几十桌酒席,人声嘈杂,此时,催上席的铜锣声已经在村头
05-22申明大肚子
村里男人大多精精瘦瘦,这可能跟平时犁田扛耙挖土刨山挑碳背树这类力气活有关。申明是个例外,他也是两女两儿一老婆
05-18端午的馒头
不禁想起家乡的馒头来。
家乡的馒头不是像如今在城里吃到的馒头,白白胖胖,蓬蓬松松。家乡的馒头是自己土里刚
05-15乡村屠户
村里八九个生产队,村大人多,差不多家家户户养猪,不说多了,一家一年养一头两头的,那是十分寻常的事。这样算来,
05-13杵毛芽
杵毛芽是村里的土话,虽然形象,要解释清楚却也要费一番口舌。
杵就是棒杵,村里俗称忙杵,是一根长条形的圆木
05-11秋收后的田野
晚稻收割之后,太阳依然整日朗照,原本金黄如毯的田野顿时空旷而宁静。昔日掩映在稻浪之下的田埂,此时又恢复了原先
- 上一页 1234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