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散文热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散文突然以令人惊讶的竞技状态在商品化的文学赛场上接连击败众多强大的文学对手,像一个二流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那么它内容之清明干净犹如这运动员以漂亮的姿态通过药检,就更让人疑窦丛生了;在后现代语境中,其它文体谁个不心驰神荡暗服洋药而在检验单上留下些稀奇古怪成分?散文却仍是那样的淡定与老派,追新逐异的文学市场青睐上它,究竟吃错了什么药?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下九十年代散文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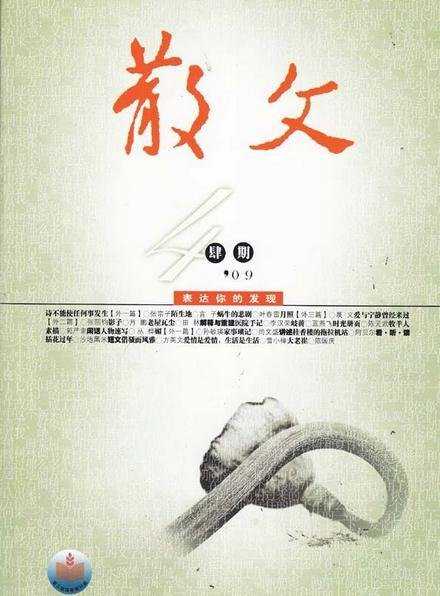
一、九十年代散文热的心理动力
理论界也仍旧那么麻木或自大。连文学资格都成问题的散文历来就缺乏学术关怀与学理支持,那么萎缩在边缘上,委身于中学课本中,中兴了又怎样?得到的仍是忽视,或者失语。
在小说家、诗人、文学编辑,以及正宗的文学研究者意识里,文学的内涵与价值指向是清楚的:生活情状描画、想象力张扬与诗意营构一向被锁定在他们的理想与视野里。“美丽的谎言”总是超越性的、虚拟性的、艺术化的。那是“创造的心灵”纵身一跃的作秀。艺术史的惯例也启喻他们,作者对真实的“自我”是毋须“实话实说”的,那“文”大可不必实写其“人”。置身于九十年代“散文热”,这些人忽然就有一种莫名的欲望躁动在心里:一种要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家庭状况、情感体验、意识状态“实话实说”的冲动。一种“告白自我”的非文学化诉求。这种冲动与诉求与他们作为某种艺术想象和隐秘心理的代言人时的冲动与欲望是完全不同的,此时他们只想以“文”写自己真实的“人”,为自己的存在画像,证实和体验对自己生命的真实持有,而不是去担当超越个人的艺术精神和时代使命面向人类说话。也就是说,九十年代大量小说家、诗人、文学编辑、各类学者不约而同加入散文作者行列,是散文的内在活力从反向激活了他们心中潜藏的另一种需要与欲求。用荣格的话说,就是激活了“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艺术家”中前一种角色的内在需要与欲求。
“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是世俗化、社会化的饮食男女,短暂脆弱的生命个体,与世上的芸芸众生并无二致。在“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和变动不居的大干世界中,亦如流萤一闪,沧海一粟,其生存的无根之感和湮没与丧失“自我”的忧虑与恐惧是与芸芸众生一样深埋在潜意识之中的。在那个文学的虚拟世界中驰骋想象力时的忘情忘我,常常替代或遮蔽了他们对自己真实处境的直视和对自己生命有限性的体认。遭遇九十年代“散文热”,扑面而来的那种人的“自我”复苏后的清新自然气息,那种对人性丰富性的体认与张扬,对生命存在的叹喟与价值吁求,显然是从“人”的层面触动了“作为艺术家的个人”潜意识中对存在有限性的隐痛与对生命亲在性的自恋自重。而置身市场环境不可避免的生存紧张感和所遭遇的自我迷失与异化压力,无疑更形成他们返回内心与“告白自我”的精神动力。于是,写散文以反照自身,在存在的迷雾中确认并享受自身真实的生命与意义,寻求内心的安宁与永恒,就成为他们心中自然的近乎本能的需要。这些人加入散文作者队伍,不是追逐时尚,也没有什么形而上的高邈写作动机。他们是为了自己而写作散文。至于高邈、悠远、宏大一类写作动机,那是他们写作小说、诗歌、戏剧或学术论文时才怀拥的。
庞大的散文读者群在九十年代出现,是散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持续发“热”的更重要原因。读者可是知道虚构性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区别的。他们向虚构性文学要娱乐,那些虚拟的艺术形象必须给他们娱乐性刺激,否则便不会接受。他们向非虚构文学(包括散文)要真实,要从中可以直观人性、烛照自身、感悟存在、体会对生命真实持有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如像庄子所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他们便不掏腰包。九十年代似烈火燎原的市场经济进程和与之联袂而生的人的自觉、自恋、自重意识普遍复苏,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人内心不安、躁动、无措、失落时代的来临。市场环境带来的惶惑眩晕与自重自怜相缠结的陌生体验,使得中国人特别是老百姓心理普遍处于焦虑状态。人们内心都在渴望抚慰,祈求安宁,寻觅生命价值的妥帖归宿。然而人们来不及细想就被卷进拜金主义的浪潮随波逐流,在冰冷无情的市场环境中接受启蒙、冲击和重塑。温情没有了,家园远去了,心中已不再有和煦的爱的芬芳和绿色的梦的阴凉。这不适,这隐痛,如何诉说?心中五个去处,四下无人求助,自言自语,自聊自慰也就成为人们心理的自然走向。九十年代中国小说、诗歌、戏剧业余作者锐减而散文园地业余作者激增,正是散文自说白话自聊自慰的文体功能吸引了众多有文字能力的老百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读散文找到了与自己对应的情绪与体验而获得抚慰和宣泄。德国美学家沃林格揭示过这样的道理:“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心理需要”(《抽象与移情》)。九十年代散文遇合与满足了中国老百姓的深层心理需要,焉能不热?
可以说,九十年“散文热”兴起,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对文学领域影响的合规律性表现。散文以从未有过的普及被书写和阅读,并在大众语境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真诚、自然与放松,显示了真正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从创作心理看,九十年代散文心理的主要走向有两股脉络,都是重回人的立场后与时代的互动及回应:一是内倾的,走向人性完整的“向内转”。借用沃林格那深为荣格赞同的说法,即人内心寻求安定与永恒的“抽象冲动”。在沃林格看来,从原始时期开始,人面对外在世界变幻不定的迷乱和威胁所引起的内心不安,会促使人把自己与现实世界的关联降到最低限度,以摆脱惊惧不适的感官痛苦,退回内心去寻觅安息之所。沃林格认为这是人未受玷污的心灵的本能倾向。以此观看九十年代中国散文庞大的作者群,于时代巨变所引起的惊惧不适与茫然无措中,返回内心去寻觅心灵的栖息之所,确实于他们是一种纷繁的共通,具体的普遍。在他们的作品中,降低自己与现实世界关联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回忆:沉浸入漫漫的往事回忆;二是回家:从栖居之家到精神家园;三是庸常感受放大:从常情琐事诗意化到小男人小女人式的自顾自怜。 ,
回忆是珍视生命、品味和持有生命过程的自然方式。由于人的自觉和世事的巨大变迁,往事的价值增加了,怀旧成为扩展心灵广度与深度的有效手段。恰如法国作家辛涅科尔所说:“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人们怎能不对自己的往事倾注更多的依恋、更多的悲欢!九十年代散文在都市化、市民化、商业化的喧嚣背景中退人沉思与怀旧,可视为中国人在自发地弥补心灵的欠缺和维护与传统的联系。其回忆往事中乡情、友情、亲情及童心童趣一路,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张中行的负暄系列、张洁的《世上最疼我的那人去了》、冰心《我的家在哪里》,乃至新锐作者张锐锋的《小河》、《大河》,庞培的《乡村肖像》、《摇面店》等,弥漫了文化乡愁,虽所忆之事多在物质贫乏年代,然愁思之声哀而不伤,对生命的温馨爱意与清醇
的人性美跃然纸上。而回忆中苦痛悲愤一路,如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等,则寓深广的幽愤于平实从容,融尖利与深邃于苍凉厚重,极见精神修炼,显示出在个人坎坷的精神痛苦中承受历史苦难的能力。两路回忆汩汩滔滔,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出,皆风韵真淳,情性自然,使九十年代散文既续接上了传统散文气脉,又富于现代感。
“回家”是九十年代散文的又一母题。在对外部世界茫然无措和无能为力的感受中,“家”的意义与地位提升了。“回家”既是降低与外部世界关联的一种退缩,也是对个人身份和人性完善的回归。当人的生命之舟在社会的滔滔浊浪中颠簸沉浮的时候,“回家”是怎样一种心理诱惑啊!家是安全的港湾,家是温暖的巢窠和自由的彼岸。九十年代散文在“回家”母题的表现上有互为补充的两个层次,一是对作为生命发源地与亲情纽带的栖居之家的依恋与吟唱,二是对作为人精神根基的精神家园的迫寻、探问与皈依。前者由于植根于人性深处而在九十年代散文作家作品中有着普遍表现,如裘山山的《黑白人生》、姜德明的《家居琐记》、韩石山的《女儿的嫁妆》、王璞的《何须说感谢》、汪政的《菜谱》、素素的《心念到永远》等,其天伦温暖、亲情至深的娓娓叙说,把人天性一面的温馨与美丽点染得极具魅力。而众多感念家乡,吟唱故园的专集,如周同宾的《皇天后土》、刘成章的《羊想云彩》、张放的《家园的味道》、陈明云的《竹海天外风》等,则把诞生他养育他那片土地怀拥亲吻吟唱为诗,显示出心灵回归、精魄安顿者十足的沉醉与陶然。精神家园的探寻、叩问与守望者在九十年代散文作者群中属于为数不多的智者,如《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守望的距离》的作者周国平、《庄子现代版》的作者流沙河、《荒芜英雄路》的作者张承志等,面对身外的滚滚红尘与世相百态,他们规避独善,冷眼深思,在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探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归宿。其痛苦的思索与紧张的追问之中,一种先哲般的清明灵睿、东方式的人生智慧如夏日清风为散文界带来了思想的清爽之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下,这类作品显示出这一时期散文在人性回归问题上达到的精神标高。
庸常感受放大是九十年代散文应世写人最具现代意味的部分。面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与巨变,这些散文作者在心理上“向内转”,不是转向传统道德人伦寻求价值支撑,而是与时俱进,在庸常生活琐屑题材的现代感受上竭力扩张自己,充实自己,以冲消自己的不适与迷惘,张扬生命的欢乐与品享。庸常感受被极力放大,外面的世界就变小了,不再构成失落与不安的源泉,一己生活的狭小空间被扩张到了视野的极限,到处贴满了个人生命的独特意义与个人感受的独特印记。出现于九十年代中期的《都市女性随笔》十四册,即把开放社会与商品文化中女性的自我圆融与自得自足彰显到极至。都市情调的庸常生活凡人琐事被性灵化精致化得宛如鲜花朝露,时尚而另类。笔意由俗写雅,直追张爱玲、苏青散文的柔媚灵慧。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力、参悟力与软性的自持力使这类“小女人散文”充满了人生别趣,成为九十年代散文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九十年代散文创作心理的另一基本走向是外倾的,体现人心智扩张性与包容性的“向外转”。沃林格曾借用德国美学家立普斯的理论,将这种为对象灌注生命与意蕴的心理倾向称为“移情冲动”(《抽象与移情》)。在沃林格看来,移情倾向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是人的心智在外部世界中感受到自身存在后向对象的扩张与渗透。主体心智倾注于对象并在对象中玩味的,实际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是自己的艺术意志与生命力。“移情冲动”于人类可视为在思想解放,理性高扬时代必然发生的一种心理倾向。九十年代中国文人遭遇到坚硬冰冷的市场经济环境,普遍沦为失败者而退回文人立场,退回室内。但此时中国社会的开放心态与宽松思想环境却极大地激发起他们在室内驰骋心智、扩张自我的表现欲望。这当然不是说他们又再度萌生了要去作社会的精神领袖或思想导师的妄想,是指他们陡然感悟到自己身上人文智慧的活力而怦然心跳。毕竟深潜在血脉里那儒道互补的传统人文精神余脉是不容他们沉沦的。收敛回内心的激情在室内转化成为自由悠思和人间关怀,使他们纷纷借用散文这种自由随便的载体在广阔空间去挥洒自己的智慧之爱。九十年代散文园地出现的盛极一时的文化散文、学者散文、书话散文,正是中国文人潜在的生命力在特定时代的又一次复苏与出征。
作为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热”的呼应,文化散文显然是中国文人将自己的内在状态转化为外在强势的便捷途径。哪怕世事成荒野,我有文心可雕龙。他们在历史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世俗与审美的关联纠葛中纵横捭阖,在“文化”的宽阔视野中言说自己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感悟到的精神内蕴。这类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常表现为二位一体,文化散文是就散文的题材内涵而言,学者散文是就散文的作者身份而言,两者都有着“学者的人间情怀”(陈平原语)和专业的知识背景。如钱理群、陈平原、葛兆光、葛建雄、刘小枫、赵园、韩少功、张中行等人的散文,其散文化的言说文化方式的知识品位和人文关怀,显示出真正的中国文人在社会转型期的独立品格与和谐深沉。从边缘地位向社会委曲介入与优雅移情,这类文化散文其传统文人的心性底气与现代学者的眼界意识相融合,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颇令读者眼亮与尊敬。余秋雨于其中是个特例。余秋雨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九十年代名噪一时,其学人眼手人文意味在文化散文滥觞之初确有开风气领风骚之时效,其文的大众化品位与极强的煽情性作为文化散文之一路,也正好满足大众口味。走红于他并非浪得虚名。后来他在文人圈中遭讥讽,受围攻,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公案,盖因太热衷于从后台走上前台,显导师欲,作明星状,缺失了抱朴见素的传统学人心态。“文革”劣迹被披露后仍劲仗十足毫不收敛。文坛于是愤慨而起嘘声,义士于是血涌而张挞伐,由人而及文,泼脏水而及婴儿,因人废文的痼疾不幸再次重现于中国文坛。从心理动力角度看,余秋雨于“文革”中作为“左派”枪手的露脸和九十年代中作为文化明星的露脸,以及文坛义土对余秋雨文饰、矫情、作秀的缺乏理性深度的讨伐,皆出于同一种心理冲动:过度移情。过度移情希冀自我从对象中获得过度显示与过度补偿,而这是极易丧失移情冲动的本色与天真的。
相对而言,九十年代的书话散文倒是更文人化和更富书卷气的文人精神张扬。坐拥于书城,开卷净土,闭门深山,将精神拥抱了精神,把文心贴接了文心,濯足春水,坐看云飞,仰俯自如,此乐何及。那寻书、购书、藏书、读书中的人生品味,那发于书香的所思、所感、所悟、所爱,舒徐悠缓地浸淫在性灵鲜活的字里行间,表达着九十年代中国文人最优雅惬意的精神漫游与远征。这一时期的书话较之以往,不
仅性情味更足了,而且心胸更扩大开放,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内容。如孙犁、姜德明、舒芜、黄裳、张炜、朱学勤、王晓明、南帆、陈子善等人的书话,书里书外,书人书事,从容洒脱间都有社会人生意味的贯通。虽性情各异,旨趣纷呈,但都不隐逸,不内敛、不消沉。书斋中的人间情怀与人文气息,犹如繁枝密叶间透出的点点阳光,温煦地洒落在九十年代读者心田里,为读者照亮了一片他们视野以外的充满睿智雅趣的新天地。
当然,九十年代中国散文作家的移情也并不都是温厚舒缓的,基于某些震撼性经验,或者出自内心卓尔不群的个性,一些散文家愿意在现实面前采取一种搏斗的姿态,向大众展示他们批判的犀利剑术。恣肆放纵是这些宽松时代思想自由的勘探者进行社会批判时的情感状态,而批判的精神根基则是对剧变时代驳杂生活的因爱而恨。这类以思想颖悟和犀利为特征的散文家可分为两个年龄层:一是以邵燕祥、李国文、流沙河为代表的7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是曾坠人深渊历经磨难并从此与社会弊病终身为敌的一群不死的啄木鸟,自重新获得飞翔的自由即无时不在以利喙寻找蛀虫们隐蔽的洞穴,并把激情注入一次次有力的啄击。邵燕祥以始终不渝的反专制呐喊使他成为九十年代政治淡化背景中最具政治性的散文家,从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中生长出来的对时代生活的警惕和洞察,令他杜鹃啼血般不断重提纳粹屠犹、苏联肃反、中国“文革”等历史惨剧,呼吁在商品熏风中沉醉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而李国文的愤怒则猛烈倾泻于他的同行,那些无德无能无聊无耻既“左”又僵且永远不甘寂寞的文坛耆宿们。终其一生的透彻观察,吃过大亏的痛楚记忆,融合进他博杂丰厚的历史知识,那以古讽今的言说方式便有了庖丁解牛般的精准和醍醐灌顶般的痛快淋漓。流沙河批判的诗性来自他的诗人气质。虽然同样下过地狱,意绪难平,但那颗诗心以为“世事沉浊,不可与庄语”,侧面迂回出击才是更妙的方式。一部《Y先生语录》、一部《庄子现代版》,别致而幽默地表达出他与世风流俗誓不两立的决绝与深邃。另一年龄层次是以王小波、李辉、张承志为代表的年届不惑或知天命的中年人,他们是在人生最好的年华经历了中国社会最剧烈折腾与巨变的一代人中最敏于反思与长于洞见的思想者。自觉地运用人类的精神资源来勘探与追问社会现象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并且那思想力也有吻合其个性的自然与和谐。王小波的异国阅历与智者心态使他的说理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实温良的口吻,其中的调侃、幽默与入骨的批判完全没有火气,让人看到的是一种少见的儒家诗教风范;而李辉《沧桑看云》给人的印象是客观、精细与冷静。他写文坛耆宿们的是非恩怨时心理距离始终保持得较远,但其透彻的洞察力与敏慧的同情心却使他与当时的真人真事真情真心走得很近;张承志的批判永远充斥着古典的悲怆与英雄主义震雷惊电般的激昂,这是信仰崩塌时代心灵回归宗教之后获得的补偿。这一代人在心理健康与思想维度上显然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但在情绪与体验的震撼力上则逊之,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经历过炼狱里的痛苦。
总之,九十年代“散文热”兴起,是进入解放、发展与自由状态的中国人心理共性的必然反映。它让我们体验到了自我敞开,与自己融为一体并得到自由表达的真正愉快。无论“抽象冲动”还是“移情冲动”,都是九十年代散文受到普遍钟爱的价值之源。这种心理共性总体上是趋于软性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是由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基因所决定,如同我们的皮肤和头发一样难以选择,亦难以以此认优劣。有些论者视这种心理共性为“精神上道德上的衰退”,“浮滑的时代精神的表现”①,似乎偏激。能够让众多中国人自由表达并“直观自身”的文学无论如何都是有其合理性与生命力的。只要时代仍然开放,人心仍然自由,这种表达与直观就将继续下去,即便它并不峻切,并不先锋。
二、浅谈九十年代散文热
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个奇特的年代。经历了诉说疼痛的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已渐渐从文革的阵痛中走了出来,作家已不再将目光仅限于对革命叙述等宏大主题,而是逐渐将话语转向普通大众的生活。促成这场声势浩大的转型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市场经济开始以蓬勃的姿态向前猛冲时,旧有的价值观念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在文化方面,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西方思潮就如同滚滚潮水涌入中国。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文化更是汹涌澎湃地涌向中国,中国人的传统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90年以后,涌进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就已不再仅仅是对中国的发展有利的那一面,西方文化的糟粕也同他们的精华一起注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文学,作为表现人的精神生活,描述人的现实生活的艺术之一,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媒体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大众媒体已变成人们接受文学的主要方式,媒体的宣传对文学作品的普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九十年代——散文的盛宴
纵观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五四时期,思想空前大解放,作为五四运动的产物,当时的文坛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散文的丰收。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还肩负起文以载道的重大历史使命,那么九十年代的散文的丰收则是九十年代文化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九十年代的散文热,首先表现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的增多。
在这些作家中,除了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之外,九十年代还有另外一大批数量庞大的散文家群体。他们有的是从诗歌等其他领域转型过来的,如舒婷等在八十年代专注于朦胧诗的诗人。很多老作家也在九十年代获得出版市场的青睐,他们的作品被重新出版。如林语堂、周作人、张爱玲等。
除了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增多之外,散文的类别也被大大地扩展了。各种流派的散文如雨后春笋,迅速涌进散文市场,并占领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以汪曾祺、张中行、谷林、桂苓、止庵为代表的性灵小品散文的写作;以余秋雨、李存葆、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张承志、周涛为代表的宏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黄裳、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海男、韩小蕙、翟永明、铁凝、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等等。创作主体和散文文体的扩大都是九十年代散文热的表现。越来越多的作家甚至普通文学青年选择用散文的方式书写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与此同时,大众曾经作为单纯的读者也加入的散文的写作群体中。
2、一个作家、一本杂志
1.)九十年代散文代表作家——余秋雨
提起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就是余秋雨现象。不管如果评价余秋雨所提倡的文化散文和他本人的作品,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确为当时的散文注入了一股新风,引起了一场散文界的变革。
散文在经历了文革的革命文学写作模式后,已经变得疲惫不堪,它背负了太多意识形态的重荷,歌功颂德的宏大主题已经成为散文的内容。文革之后,散文还没有完全从文革的革命写作中走出来,它正在等待着一场革新,一场由内到外解放散文文体、扩大散文内容的革新。七八十年代,随着解放思想运动的展开,许多作家纷纷把笔触伸向了更广泛的对象。
2.)一本代表杂志——《美文》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陕西无疑是收获最大的省份。除了日渐崛起的陕西作家群及其高水准的作品外,各种文艺类报纸杂志的数目也是惊人的。除了贾玉萍、陈忠实、路遥等名家外,还有一批居于二线的作家也始终笔根不辍地书写着他们的故事,如冷梦、刘成章、叶广芩、红柯等,他们的作品也相继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国家性的大奖。在这种浓烈的文化氛围下,文艺类的书籍杂志也就有了发展的肥沃土壤。由西安市文联主办的《美文》杂志便是其中的一种。
《美文》自创刊之日起,便称自己为“大散文”月刊,其主编贾平凹本身就是活跃于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贾平凹提出的“大散文”口号,正是为九十年代的散文热刮了一场势头强劲的东风。
首先,他们提出的“大散文”概念旨在提倡一种有大境界、大格局和大气魄的散文,这里的大境界、大气魄和大格局并不是指宏大叙述的主流传统,《美文》所关注的更多是贴近日常生活、贴近心灵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看起来漫不经心,没有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或是主流写作需要的英雄人物英雄故事,但却更加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美文》倡导的“大散文”其实就是贴着生活的作品,真正的生活是在一点一滴的小事里,而只有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另一个层面上说,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也才称得上是真正有境界的。
其次,《美文》杂志的作者群体的庞大也是它成功的不可小觑原因。正如主编贾平凹所言:“不要以为文章都是文人写的,什么人都可以写,什么领域都有美文,大雅者大俗,大俗者大雅,如此而已。”(注:贾平凹《读稿人语》,《美文》1992年创刊2号。)“我们这份杂志,将尽力克服我们编辑的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任何作家、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未来作家、诗人、小说家、批评家、理论家,以及并未列入过作家队伍,但文章写得很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只要是好的文章,我们都提供版面。”由此看以看出,《美文》并不是以往传统中只有文人学者写作的刊物,它的作家群很广,无论是老一辈的学者散文家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甚至是中学生,只要是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文章,《美文》都不会拒之门外。也正因此,《美文》所表现的文学世界就更加的广大了。
除此之外,《美文》刊登了很多外国华裔的优秀散文作品。这对现有的散文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推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生活的表达也是各有各的特点,这种沟通也是一种相互借鉴的过程。